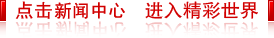村路
在我印象里,村路是被一串脚印牵来的。当初,一定是有人从很远的地方走到海边,搭建了一处栖身之所,从此,海边上飘起第一缕炊烟。后来,更多的人追着脚印赶来,更多的人家聚成了村落,脚印就变成了村路。村路形同村子的一条心脉,伸向远方,传递着内外信息,迎送着熟悉与陌生。
天气晴好时,阳光下,村路更像一条灰白的绳索。沿它走下去,会走到另一个村庄,再走,又是一个村庄。路没有尽头,无数个村庄却像绳结一样被连在一起,一个村里发生了什么事,沿路的村庄很快都知道。
海滩上的风随着季节吹来,恍若一夜间,收走了寒冬,送来了暖春。就在这悄然变换中,洼淀里的冰化了,苇塘芦苇钻出尖角,水草地也汪出一层嫩绿。芦苇和水草长得疯快,几个春阳走过,仿佛没来得及梳理,它们就连成片,葱葱茏茏铺满大滩。这时,我们肩起扁担,拿起镰刀,去给院里那些“嘎嘎呀呀”吵春的鹅鸭割青草。大滩里,水气的凉爽混着青草的馨香,像趟不透的月光一样浓厚。它们从袖口裤脚钻进来,一如母亲柔软的手掌轻抚着肌体,心绪像快乐的小鸟在草滩上肆意放飞。海风一刻不停地刮来,苇草也一刻不停地伏扬舞动。头上几只鸥鸟掠过,惊悚地大叫几声,又飞远去。我们知道,鸟这样叫,是我们的到来威胁到它们的巢穴了。青草割足,日头还早,仍憋不住分头捡鸟蛋,即使过去不止一次挨过鸟的袭击。我们在草丛里躬身隐行,脚步悄无声息,极像一场神秘的偷袭战。捡到的鸟蛋用衣衫裹好,挂在扁担稍带回家,孵小鸟。鸟蛋放在纸箱里,垫一层棉絮,盖一层棉絮,等小鸟出了壳,就精心喂养着。小鸟长出翅膀,便放到院子里,看它们在树上地下飞起飞落。偶尔,它们落在肩头上,叼叼你的耳垂,鹐鹐你头发,尽情地撒娇。鸟儿长大,就飞出院落,飞到草滩去做自己的窝,恋爱结婚,生儿育女,很少再回来。
多数时候,捡的鸟蛋是带不回家的。我们捡了鸟蛋被鸟妈妈发现,它们盘旋在我们头顶凄厉地哀鸣,不一会,几十只甚至上百只鸟全来了。它们盘绕着,叫喊着,接连不断俯冲下来,用尖利的嘴鹐我们的头,用蒲扇般的翅膀掴我们的脸,把鸟粪拉在我们身上。这时,我们只好把衣服缠在头上当护罩,蹲身藏在草丛里。等鸟群散去,还要把鸟蛋送回鸟窝,不这样,你是走不出大滩的。结果是,你被鹐的头破血流,我被掴的鼻青脸肿。村头土墙根下,老爷爷瞅着我们的狼狈相,笑颤了身子,烟锅灰都抖散了。笑完,他们伸长脖子,挥着烟袋恨恨地说,谁把你们从窝里掏走,你爹妈会咋样?鸟有灵性,惹急了它们,会鹐出你们的小眼珠!
秋天,芦苇吐穗,水草结籽,野蒿长得树一样高,它们都长成了填灶的柴。这时挑柴捆的扁担稍,多了几串苇杆穿的鱼、马绊草绑的大河蟹,挑着扁担走,好似挑着整个秋天呢!
大滩上泥浆像油脂,又粘又滑,经年不干。我们挑着草捆,勾着脚趾,一擦一滑奔向村路。即便这样,也常滑倒。赶上风大,草捆被风吹得来回晃,行走更不稳,摔的跟头也更多,甚至前行不得。这时,村路就成了艰难跋涉中极想抓住的一根稻草,恨不得把它扳到自己脚下来。等上了村路,脚板走在坚硬路面上绝不再打滑,纵然路再长,挑着草捆也能轻松顺畅地回到家。
村路总是那么简单而安宁,默默托载着匆忙脚步、负重的车轮,但没人会想到脚下就是和村子一块诞生的村路,甚至连它的名字也被人们忽略了。可是,村路却记着路上发生的每一桩事。
那年,大滩里稻田插上秧,瘸脚二哥悄悄离开村,村路捎来信,他是去了燕山脚下的采石场干活。半年后,瘸脚二哥从山里带回一个哑巴姑娘。哑巴姑娘长得壮实丰满,模样俊俏,一笑,眼睛眯成两弯月牙儿。年根下,瘸脚二哥和哑巴姑娘圆了房,哑巴姑娘变成哑巴二嫂。第二年生下一闺女,隔一年,又添一儿子。瘸脚二哥还在燕山里,每一两个月回趟家,就这样,一家人日子过得有滋有味,哑巴二嫂出出进进,笑容像百合花一样妩媚。可是,那年冬天,外来的一辆双排座停在哑巴二嫂家门口,匆忙把大人孩子接走了。人们并没在意来的是谁,为啥把他们接走。第二天中午,村路上老远传来嚎啕声,谁也没料到,那辆双排座拉回瘸脚二哥的尸体。瘸脚二哥是在山坡上被滚下的一块巨石压死的。人埋了以后,哑巴二嫂半个月没出门。人们再见到她时,脸上笑容没有了,人似苍老了十多岁,但目光里却多了一个女人少有的坚毅和刚强。她对母亲比划说,她哪也不去了,就在海边扎下根,好好把两个孩子拉扯大。听着年纪轻轻的哑巴二嫂这么说,母亲掉下泪。哑巴二嫂读懂母亲泪中的含义,她摇摇头,挨近了母亲,掏出巾帕微笑着给母亲擦泪水。这以后,哑巴二嫂学会了织网、补网,学会了摸鱼捉蟹、赶海和种稻子,牛马一样托载着她那个不完整的家。
有天傍晚,天已黑透,哑巴二嫂满脸汗水跑进我家,跺着脚冲母亲哇哇大叫,说她五岁儿子小石头不见了。我们全家在村里找了一遍没找到,最后不得不求助村长发动村民帮忙。瞬时,村路上、河岸边、大滩里,无数条手电光伴着声声呼唤划破了夜空。哑巴二嫂不会喊话,听不见呼唤,但她知道人们正在尽心竭力地寻找孩子。哑巴二嫂站在村路上,转着身仰看那些手电光,突然揪住头发哇哇哭嚎,哭声凄惨,揪心扯肺。不知怎么,这一刻我忽然想起草滩上鸟妈妈的凄厉哀鸣,想起盘绕在我们头顶上的鸟群。当人们把睡在稻场草垛里的小石头找回来,哑巴二嫂疯了一般搂紧小石头,脸颊贴着孩子,扑簌簌泪水流成了河。从那以后,我就再也没捡过鸟蛋。
大滩上苇草年年绿。草滩深处多了哑巴二嫂和她俩孩子的身影。哑巴二嫂背着山一样的草捆走,俩孩子背着小草捆走。看着他们趔趔斜斜走向村路的背影,我们突然觉得,大风和泥滩带来的行走艰难都不算什么了,浑身也生出一股征服一切的勇气。赶海时节,哑巴二嫂依然带上她的孩子,在平阔水滩里,她教他们怎样拾扇贝、捉鱼蟹、捡海螺。回家时,孩子累了,哑巴二嫂背上背一个,怀里抱一个,腰间套上绳,拉着盛满海鲜的笸箩向岸边走。人们看不惯哑巴二嫂近乎残酷地对待孩子,都好言相劝。可哑巴二嫂总是比划说,孩子不能太娇惯,得让他们从小学会生存本领!孩子到了上学年龄,假日里,洼淀、河边、稻田内,常见她带着一双儿女劳作的身影。哑巴二嫂在生计路上拼命跋涉,她的孩子也在凄风苦雨里茁壮成长。最终,哑巴二嫂把孩子双双送进大学校门,成了村人敬仰的了不起的人。
几年后,哑巴二嫂站在村头,把出嫁的女儿送上了村路,接着,又把儿媳从村路上迎进家门。儿女都在大城市干着大事,哑巴二嫂不愿去大城市住,仍守着她和瘸脚二哥的老屋。她舍不得离开那片大草滩、那片海,更舍不得离开和她相濡以沫的淳朴善良的海边人。
天好的时候,哑巴二嫂常站在村头,望着远去的村路,淡定目光里含着安详。哑巴二嫂一辈子没说出一句话,可她把一辈子的事都清清楚楚写在了村路上。风撩动着她的白发,哑巴二嫂站成了一尊母亲雕像。
村路还是老样子,连着村庄,伸向远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