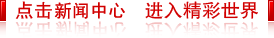遣返
这是四十三年前的一段往事。
九月里,秋高气爽,正是农场打秋草的季节。那天清晨,我正蹲在宿舍门前的空地上“唰唰”地磨着镰刀。忽然,从队部方向传来阵阵口号声。
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!”
“誓死保卫毛主席!誓死保卫党中央!”
“狗崽子XXX从农场滚出去!”
我听得真真切切,那“狗崽子”恶名之后连缀着我的名字。
说时迟,那时快。几十名臂佩红袖章、手捧红宝书的红卫兵已喊着口号来到宿舍前,并在我面前围成一道弧形的人墙。我霍地站起来,下意识地扔下手中的镰刀,深吸了一口气,静候着厄运的降临。
“根据上级指示,从即日起将狗崽子XXX轰出农场,遣送原籍守盐庄改造。”宣读遣返令的是队上红卫兵组织负责人,一位平素老成忠厚、待人谦和且寡言少语的工友。
“我不走!也没有理由轰我走!”一向逆来顺受的我,此时却做出近乎勇敢的抗争。“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,《宪法》保障公民的居住权和劳动权。我的户籍在农场,我哪儿也不去!”
“文革”似汹涌的洪水,早将共和国的法制体系冲垮。连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命运都岌岌可危,我却和一群红卫兵奢谈起神圣的《宪法》来,真是不识时务啊!
“他不走,咱就动手!”人群中一阵骚动。
站在前排的红卫兵老阎和小董向我使着眼色,把我推搡进宿舍内。小董说:“老秀,好汉不吃眼前亏啊!快打行李吧!”我仍执拗地在那里琢磨《宪法》条文,没把打行李放在心上。老阎道:“你不打,我俩打。谁让咱们工友一场呢!”
行李卷刚打完,便有人来叫阎、董二位去开会,并顺便通知我:“午后开你的批判会,谁让你不痛痛快快走呢!惹骚了吧!”
四壁尘埃的小屋里,只剩我孤零零一人。屋内屋外阒寂无声,只偶尔听到从八农林带上传来的秋蝉的凄叫。我坐在光板儿床上,斜倚着行李卷陷
入了沉思。
一年多前的春夏之交,我来到五分场七队。在农工们的帮助下,我这个书生也学会了牵马耙地、插秧拔草、割稻打场、挖河修堤。艰苦的田间劳作常累得我腰酸背痛,但结识了那么多淳朴善良的农工朋友却让我感到幸福和满足。闲暇时我给工友们记考勤,替他们写家信甚至情书,给他们讲《三国》、《水浒》的故事。就连“文革”以来那贴满墙壁的大字报也多数由我代笔。风吹日晒使我原本白皙的皮肤变得黧黑,我俨然成了一个道地的农民。然而,突如其来的“文革”狂飙摧垮了我的“农工梦”。偌大的中国,何处是我的安身之所呢?
中午,同屋的大李和小李给我打来一份饭菜,心事忡忡的我如何咽得下?小李说了几句宽慰我的话,大李则说:“你这一走,谁给我们讲《水浒传》啊?”我听了,只有苦笑。
批判会在队部大食堂前的空地上进行。我被带入会场时,人群里响起一阵那年头全国通用的口号声。作为被批判者,我受到了意想不到的礼遇:没让站高凳、没让坐“喷气式”、甚至没让我低头。我穿了一件新换的衬衣,左胸前别了一枚毛主席语录牌,端立在秋天的阳光下,在人群中寻找那一张张熟悉的面孔。
一位原籍山东的工友第一个发言。
“XXX!”他大声喊着我的名字,“你来七队一年多了,你的表现,俺贫下中农可是看在眼里、记在心上。”我的什么表现被他们看在眼里、记在心上呢?我正满腹狐疑时,这老兄又继续发言了。“要论劳动,你可没的说。风里来、雨里去,不怕苦、不怕累,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了嘛!”天哪,这究竟是批判会还是表扬会呢?这位工友似乎察觉到说走了板儿,连忙话锋一转:“不过,你出身不好,要和反动家庭划清界限嘛!和群众对着干,是没有好下……是没有好出路的。”
其他几位工友的发言,也大多语气平和,无非是提醒我正确认识群众运动,告诫我与家庭划清界限之类的话语。没有激昂慷慨的陈词,更没有“踏上一只脚,让你永世不得翻身”式的咒语。一场批判会开得如此“温良恭谦让”,在疯狂的年代里怕是绝无仅有的吧!
批判会草草收场,工友们又都下田打秋草去了,老阎和小董则送我踏上
了遣返之途。当三辆自行车行到队部西头时,路边土屋里出来一位妇人。啊,那不是侯嫂子吗!
“兄弟,你可千万别想不开呀!”侯嫂子抹着眼泪说,“往后的日子还长着呢,好人总有好报的,听见了没?”
老侯家是队上头等困难户,夫妻俩拉扯着四儿四女共八个孩子,日子的艰难可想而知。上一年冬天,我曾把自己的一件棉袄送给侯家大小子御寒。为这件小事,侯嫂总心存感激。
离开七队地界,我们一路北行,三个人谁也没言语。临近八用支桥时,老阎突然问小董:“人家守盐庄要是不收老秀,那可喒办呢?”
“不收?不收正好啊,咱哥仨就手打道回府呗!我说老秀……”小董似乎想起了什么,“咱俩那首《农垦工人进行曲》还没谱完呢!”
小董原籍张庄子,初中文化,爱好音乐。他说的那首歌就是由我作词,二人合作谱曲的,到今天我仍然能哼出那歌的旋律。
我们在总场供销社门前歇了歇脚,由小董掏腰包买了二斤玫瑰香葡萄。三人美美地吃了一顿,这才驱车东行。来到守盐庄村口时,已是红日西沉的傍晚时分了。
三人来到大队部,阎、董二位向村支书说明来意并递交了分场开的一封信。
“这个人我们不能收!”支书的态度很坚决。“第一,他是农场工人不是四类分子,应该在农场就地闹革命嘛!再者说,城里的“黑五类”还赶点地往农场送呢,你们农场喒还往往外轰人啊?”他看了我一眼,说:“二叔,你先去看五爷吧!我和这二位同志谈……”这位村支书与我同村同姓,但却非亲非故。
那时,父亲住在堂兄家。我走进老人家住的西正房屋时,他正吸着烟捧读《毛主席著作选读(乙种本)》。听到我被遣返的消息,父亲的脸色一下子阴沉了。“怎么会这样?怎么会这样呢?”他不住地喃喃自语,那只捏着烟头的手也一劲地颤抖。
“当年你高考落榜,是受我牵连;前年,你被中学辞退还是受我牵连。如今,我牵连得你连农工都做不成了。莫非我真的罪孽深重吗?”说着,老人家已泪流满面。
我赶忙劝慰父亲,说了些“回村当社员也一样修理地球”之类的话。父亲仍自责不已,香烟是一根接一根地抽,不一会儿小屋里便弥漫起呛人的烟雾。
天渐渐黑下来。堂嫂端来两碗粥和一盘咸菜熬小鱼儿。父亲和我都心情沉重,谁也没动筷子。在昏暗的灯光下,父子俩默然相对,小屋内寂静得令人心悸。
忽然,堂屋响起脚步声。门帘一挑,进来了村支书,老阎、小董紧随其后。
“二叔!你跟他俩走吧!”
“走?往哪儿走啊?”
“回咱农场呗!”小董说。
“都说好了吗?可别来回折腾我呀!”
“都说好了!”支书对我父亲说,“我们向公社汇报过,公社也跟农场通过话,让我二叔放心回去吧!”
“这就好,这就好了!”父亲脸上的阴霾顿时消散。
我辞别了父亲和堂兄、堂嫂,与老阎、小董踏上归途。此时,已是繁星满天,初秋的晚风有些凉意了。
两餐未进食,我早已饥肠辘辘,但一想到要重返五农场,我便精神陡增。那边的土地等着我,那里的工友等着我。我又要和农工兄弟们一块儿打秋草、割稻子了,又要给他们去讲《水浒》、说《三国》了。我把自行车蹬得飞快,口中还哼起样板戏来:“……月照征途风送爽,穿过了山和水沉睡的村庄……”
这便是发生在四十三年前的“遣返”故事,我们曾经历过那种荒唐的年代,在那特殊的岁月里,有人变得畸形,有人依旧善良。